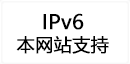第三期
- 【卷首语】为打造“北疆文化”品牌贡献力量
- 【领导讲话】弘扬“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闯出新路
- 【专稿】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精髓要义和重大意义
- 【修志札记】厘清地方史志关系
- 【修志札记】精品年鉴视域下年鉴特色内容记述分析
- 【修志札记】浅谈新时代背景下年鉴事业的新挑战、新希望、新发展
- 【修志札记】科学认知年鉴创新年鉴编纂
- 【修志札记】如何更好地发挥年鉴“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 【史记寻踪】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所见北疆边郡之历史面貌
- 【史记寻踪】清代厅县对准格尔旗汉民的管理
- 【史记寻踪】呼伦贝尔金代长城
- 【史记寻踪】丰镇月饼
- 【史记寻踪】后山抗战第一碑
- 【机关党建】自治区党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举办 主题教育第三期读书班理论学习
- 【机关党建】自治区党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举办 年轻干部党性修养提升班
- 【机关党建】自治区党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打牢民主生活会基础
- 【机关党建】自治区党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召开 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 【机关党建】自治区党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系列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 【工作动态】自治区党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与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举行书籍捐赠仪式
- 【工作动态】自治区党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贺彪一行赴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汇报工作
- 【工作动态】自治区党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举办内蒙古高等学校志、重点企业志从书编纂业务培训班
- 【工作动态】自治区党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盟市志业务处组织召开三场评审会
- 【工作动态】内蒙古自治区年鉴事业高质量发展业务骨干专题培训班在锡林郭勒盟举办
- 【工作动态】鄂尔多斯市地方志“六进”工作实现全覆盖
- 【志书选介】《内蒙古自治区志·广播电影电视志(1999-2013)》
- 【志书选介】《鄂尔多斯市志(1990-2010)》
- 【志书选介】《乌拉特中旗宣传志》出版
- 【法规文件】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专家库管理服务办法
- 【史记寻踪】清代厅县对准格尔旗汉民的管理
- 发布时间:2024-01-23
- 来源:
◆包满达
摘要:清代准格尔旗汉民始由萨拉齐、托克托、清水河三厅分管。乾隆末年,由于萨厅的撤出,又形成了两厅分治的局面。后来晚清时期,晋抚张之洞上《筹议七厅改制事宜折》,提出为准格尔旗汉民编户立籍,归周边厅县管理。该提案最终未能付诸实施,但很大程度上打破“春出秋归”的雁行制度的限制,从制度上为内地汉民移居塞外开辟了通道。清末官垦以后,清政府将准格尔旗黑界地和河套川的征租权转给河曲县、府谷县和托克托厅。这使沿边厅县实力得到了提升。
关键词:厅县准格尔旗汉族移民管理
清代沿边厅县管辖界限不是很清晰,而且管辖范围多有变化。准格尔旗的汉民起初由萨拉齐、托克托、清水河三厅分片管理。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月萨厅撤出准格尔旗移民管理以后,形成了两厅分治的局面。这以后,萨厅始终没有受理过该旗汉民事务。可以肯定,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月是三厅分管到两厅分治的分界线。即便如此,各厅县辖区仍不明确,一旦遇有各类案件,互相推诿事件屡屡出现,使移民管理总是不到位。这也成为后来张之洞提出七厅改制的原因之一。
一、从三厅分管到两厅分治
在清代前期日益安定的社会环境和清政府默许政策下,原本单一的游牧世界出现了新的农耕经济类型并日渐扩大,而它所引起的不单是经济地理变化,相应的民族地理和行政管辖都出现了变化。汉民移入鄂尔多斯以后,如何有效管理移民成为清政府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在“属人主义”统治原则下,清朝统治者采取蒙汉分治措施,蒙古归蒙旗管理,汉民归府县管治。这样,在移民聚居的蒙古地方形成了两套管辖机构。后来,为了协调旗县关系,以便有效管治各自属民,清政府在内蒙古西部先后设置宁夏理事司员和神木理事司员衙门。当移民人数较少、分布相对集中时,这种三管齐下的机制还能有效运行,在管理移民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乾隆以后,汉民活动范围不再限于边缘的伙盘地,鄂尔多斯各蒙旗腹地及沿黄河一带已遍及汉人足迹,而且进入蒙地的路线不断增多,除了从沿墙府、县能直接进入蒙地外,从周边各厅也有大批汉民移入蒙地,从而形成蒙汉交错格局。这样一来,仅靠旗、县来管治那些“人无定名,籍无定户”,流动性又很大的移民,就变得很困难起来。故清政府把鄂尔多斯各旗开垦区域,划归邻近各厅来管理。准格尔东部和北部开垦区,由归化城土默特境内各厅分片管理。起初是萨拉齐、托克托和清水河[1]三厅分管,后来变成托、清二厅管理。这里有一份乾隆五十六年(1791)萨拉齐通判发给准格尔旗贝子的信件,可以印证萨厅曾参与管理之史实。
原文汉译如下:
萨拉齐通判那富咨复鄂尔多斯扎萨克贝子,为知照事,查本通判辖地毗连贵贝子旗,凡蒙古民人交涉之盗骗等案,由本通判衙门受理会审。嗣后发生盗骗等案,务将涉案人等随时押送前来,以便及时对质审办。只审案犯,不传讯涉案人,实难结案。盗贼人等上堂不见人证物证,辄翻供不悔罪。若再行传唤涉案人等,又恐逾限拖延审理,本通判亦获罪不轻。自应晓谕各旗,文到,查阅文内事项,嗣有盗骗之案,务将盗贼及人证物证一并送来,涉案人员亦一体押送前来,以资对质审结。将此告之。乾隆五十六年三月十四日[2]。
但仅隔七个月后,情况有了新的变化,萨拉齐厅撤出准格尔境内汉民管理。对此变化档案中如是记载。
原文汉译如下:
萨拉齐通判那富致鄂尔多斯准格尔贝子,为知照事,案查,神木司员、归绥道文饬本通判尽行驱逐贵旗种地民人,奈因地界不清,旋即向托克托通判咨询。嗣后托厅咨开,前任通判等将鄂尔多斯章古图淖尔西南所有吉格斯太、哈丹和硕等地归萨拉齐管辖,章古图东南新召归托克托厅管辖,等因议决呈报上司衙门在案,概未以都日本毛栋(四棵树)渠为界之事,等因前来。故本通判将尔等两旗边界划清。自今以往,凡贵贝子旗内一切案件,皆咨请托厅办理。达拉特贝子旗内一切案件,由本通判衙门受理等因议定事宜,绘图呈报神木司员、归绥道在案。故将两旗地界业经划清,凡贵旗一切案件,悉由托克托厅受理,理应绘图咨行贵贝子知照,此咨。乾隆五十六年十月[3]。
嘉庆二年(1797),汉民乔建与准格尔蒙古丹津因盗窃事件发生争斗,旗衙门把涉案人员交由托克托通判衙门处理。当时该通判以案发地在萨拉齐辖境为由,拒绝受理,并将丹津等人送回旗里。之后,准格尔旗将此案又移交萨拉齐厅办理,但得到的答案是,“贵贝子旗如有斗殴、命盗重案,例定悉由就近归托克托厅审理”[4],最终又未予受理。这是萨厅撤出准格尔旗移民管理后,准格尔和萨拉齐双方的首度交涉。托克托厅拒绝受理显然是在推卸责任,萨拉齐厅的拒绝是正当理由,因为此前萨厅已经撤出准格尔旗移民管理。此后,准格尔与萨拉齐也鲜有信件往来,但萨厅始终没有受理过准格尔旗汉民事务。可以肯定,乾隆五十六年是三厅分管到两厅分治的分界线。
二、厅县对汉民管理的弊端
清代内蒙古的“各厅辖境以道路、山川为界”。乾隆时期,“鄂尔多斯章古图淖尔西南吉格斯太、哈丹和硕等地归萨拉齐管辖,章古图东南新召归托克托厅管辖”。至道光年间,萨、托两厅辖区略有变动,“托厅以呼斯太河、塔本毛栋(五棵树)为界,以外(达拉特旗辖地)悉归萨厅管辖,以内(准格尔旗辖地)归托厅管辖”[5]。由于辖境的不明确,一旦命盗重案在交界区发生,搭界的两厅就相互推诿,使本来很容易解决的案件迟迟不能办结。“准格尔一旗系托克托城厅与清水河厅分管,其两厅分界所处,无明白案据,惟听该旗自认,以致遇有重大案件,辄互相推诿”[6]。咸丰年间,托克托厅所辖查干敖包地方发生商民张万灵银两、衣物被劫一案,由于案发地点毗连清水河辖治区,两厅相互推诿,没有及时派人去查拿案犯。后来,归绥道派员查出案发地系属托克托厅辖治区,遂饬令该厅缉拿匪徒,但由于时间拖延过久,匪徒早已远遁,而未能拿获[7]。由于“各厅辖境不清”而弊端百出的情况下,归绥道饬令所辖各厅,“查明辖区四至,会同交界之各该厅,于边界处堆石立界,划清界线”[8]。但实情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加之蒙旗地面辽阔,大多移民又是名副其实的“飞民”。他们居无定所,来去飘忽,今在清水河管辖区,明年可能迁徙到托克托辖区,移民管理未免实有顾此失彼之虞。于是外来“游匪”,往往恃为“逋逃渊薮”,成为晚清蒙旗社会动荡不安的一大隐患。
嘉庆道光以后,清朝统治日益腐化,地方吏治败坏,导致厅官、衙役勒索成性,治民不力。清水河厅辖区南至河曲县、北至托厅,约占准格尔面积的十分之一[9]。长期以来,该厅以受理肇事民人为交换条件,强行劈分准格尔旗地租。准格尔达庆台吉恩克图鲁管辖地为清水河分治区,他所征得之地租中,“一吊钱内一概抽取二百文钱交予清水河厅,倘有奸诈民人滋生事端,该厅管治已有多年,为此缴纳之钱数量亦非少。近年来,清水河厅衙役要求一吊钱中抽取六七百文钱,若不给,即抓捕务农民人解至衙门关押,直到年末收到钱财后才释放”。光绪二十年(1894),清水河厅衙役韩四等与达庆恩克图鲁商定:从这年起,该达庆从每年征得之地租中,缴纳该厅一百七十吊钱,方可受理民人事务[10]。不然,贱民滋生事端,概不予审办。至于勒逼缴税同样普遍。地租的劈分与受理民人案件相挂钩,反映厅、县的移民管理不到位。这也成为后来张之洞提出七厅改制的原因之一。
三、口外七厅改制与准格尔等旗对寄民编立户籍的抵制清代内地汉民移入蒙地,基本上是越长城由南向北步步推进的,所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游牧八旗和鄂尔多斯沿墙地带成为汉民最早移入区。经过几代人的垦辟和经营后,移民便成了常住人口。但在清末以前,这里只“有客肌(寄)之汉族,无土著之汉族焉”[11]。起初,清政府对移入蒙旗的汉民,主要通过相当于内地保甲的总甲(或里甲)来进行管理。后因土默特、察哈尔地区的移民越聚越多,雍正初至乾隆中叶,在察哈尔右翼和土默特境内先后设立丰镇、宁远、归化城、萨拉齐、清水河、和林格尔、托克托七厅,分片管理汉族移民。
厅,原本是行省的派出机构,最初不是一级独立的行政建置。厅长官同知或通判也是非正印官,手中只有关防而无印。清政府在新开辟的边疆地区不便径设府州县,所以将厅移植过来作为过渡,并在同知、通判前加理事或抚民衔,以示可以掌管厅内的一切行政。厅因而成了特殊的行政建置[12]。
厅在土默特、察哈尔地区的陆续设立,标志着西部内蒙古亦形成旗厅并存、蒙汉分治的局面。但是,旗厅并存、蒙汉分治的体制毕竟是两种权力运行机制完全不同的系统,在许多方面是无法兼容的。同治道光以后,随着移民数量的日增和蒙旗牧地的日削,旗厅并存体制的各种弊端就显现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察哈尔、土默特蒙旗虽已农耕化,不缴课税的私垦户占多数,造成“逃户”和“遗粮”的出现;二、清末时期,口外蒙古游牧地内“无地方有司之编查”“无里正乡保之约束”。因而逃犯、马贼藏匿其间,“徒党繁众,来去飘忽”,影响了地方的稳定;三、因私垦民户不交纳地租,或加价转租,蒙人撤夺地亩等事时常发生。类似现象在准格尔也多有出现。但由于厅官权力有限,汉民与蒙旗发生争端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从当时情况看,土默特、察哈尔、鄂尔多斯等地移民数量均超出当地蒙古人数,经济势力上又占据优势地位。这种经济和人数优势与蒙汉交涉案中处于劣势的大反差,对于遥治移民的边省督抚的刺激应该是很大的。另外,晚清中国北部边陲普遍出现危机,并与上述弊端交织在一起,使边疆问题更加复杂。于是,有边疆大吏把固边与治边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一系列具体改制建议,清中兴名臣张之洞就是首倡之人。
光绪九年(1883)九月,张之洞上《筹议七厅改制事宜折》,详细条陈“缺项改革、定章补署、更议管辖、浚筑城垣、编立户籍、清理田赋、建设学校、变通驿路、筹补遗粮、添设公费、募练捕兵、议定巡牧”[13]等十二项整顿办法,请求准行。这十二项整顿措施相互关联,形成完整的筹蒙计划。其中缺项改革、定章补署、更议管辖、编立户籍,以及清理田赋等项与蒙旗有密切的利害关系,也是七厅改制的关键所在[14],尤其“编立户籍”一项堪称整套改制方案的核心,很多改制内容都围绕“编立户籍”展开,所以要想“整顿边政,非查考寄民,编立户籍,无从措手”。
口外七厅汉民多系暂居,他们虽然身在口外,户口仍在原籍,这些人通常被称做客民或寄民。张之洞认为,口外寄民“五方杂处,……人无定名,籍无定户。不特赋役,保甲难于稽考,案件人证难于查传,而奸匪之薮匿,脏盗之攀诬,词讼之波累,弊不胜穷”[15]。而七厅所交涉之各蒙旗,如萨拉齐厅交涉之乌拉特三公、鄂尔多斯郡王、达拉特贝子等旗,托克托、清水河二厅交涉之准格尔贝子等旗,虽属蒙部,但寄民众多,非各厅所管辖,于是外来“游匪”,往往恃为“逋逃渊薮”,故“编立户籍”势在必行。具体操作办法是,察哈尔都统、绥远城将军、归化城副都统派出旗、蒙各员,会同厅官,对寄居于各蒙旗的汉民每年进行一次清查,以加强管理[16]。察哈尔、土默特境内的寄民,全部分等划成“粮户”“业户”和“寄户”之办法,编立户籍。
张之洞的改制方案一旦实施,必然引起两种不同的结果:一方面,有利于清廷有效治理移民,避免“逃户”和“遗粮”的出现,增加国家税收;移民通过“编立户籍”可获得合法定居蒙地和耕种蒙地的权利。另一种结果则与此相反,即蒙旗地位和处境越发陷入困境。因为一旦土默特界内流民落户,日聚月广,流民就占据蒙古牧地,而那些“坐吃租银”的土默特两翼蒙古,因清理田赋而经济来源大大减少,蒙旗管辖权也同样受到削弱。因此,张之洞的七厅改制方案出炉之后,即遭到蒙古各旗的普遍反对。当时绥远城将军丰绅、归化城副都统奎英根据土默特两翼十二参领的联衔呈报,上奏清廷反对改制、取消编立户籍之议,并将此情况函告伊克昭盟帮办盟务巴拉珠尔,拟与鄂尔多斯各旗通力反对七厅改制。接函后,巴拉珠尔即传知各旗采取应对办法。以下是达拉特旗贝子转呈副盟长、准格尔旗贝子扎那噶尔迪的一封信件。
原文汉译如下:
达拉特旗贝子记录一次索诺木彭楚克、协理台吉等呈御前行走副盟长、贝勒衔扎萨克贝子加五级记录四次诺颜,为呈报事,本年三月初九日,兹准署理已故盟长、御前行走贝勒衔贝子盟长印务之御前行走帮办盟务镇国公衔头等台吉加三级记录三次、军功加五级记录二次巴拉珠尔札开,兹据绥远城将军、归化城副都统札开:山西巡抚张之洞奏请,拟为暂居于萨厅所交涉之鄂尔多斯郡王旗、达拉特旗,托、清二厅所交涉之准格尔旗民人,编立户籍。奉旨:著交理藩院议奏,钦此钦遵,等因前来。查《钦定外藩蒙古王公表传》,元太祖十六孙巴尔苏博罗特为鄂尔多斯济农,子袞弼哩克图墨尔根继之,有九子,分牧而处,今鄂尔多斯七扎萨克,皆其后裔。因本部为圣朝立国有汗马功劳,叙功编设鄂尔多斯七旗,赏郡王、贝勒、贝子等爵秩,世袭罔替。鄂尔多斯所有耕牧地乃我鄂尔多斯驻牧之地。察哈尔林丹汗虐我部时,七旗扎萨克郡王、贝勒、贝子等与喀喇沁、阿巴嘎诸部长等,一同大败察哈尔兵四万於土默特赵城。从此,本部归附满州,于天聪二年敬献马驼。顺治元年,选兵随英亲王阿济格赴陕西,剿流贼李自成。康熙十四年,叛镇王辅臣同党孙崇雅占据神木,贝勒固噜斯希布率兵协助大军,败逆贼,复神木。因本部历来实力报效,诏封郡王、贝勒、贝子有差,世袭罔替。本部不归属归化城、萨拉齐、托克托、清水河等处同知、通判。本部所有台吉、官弁、喇嘛等向以耕牧兼营,维系生计。近年来,内地民人来我蒙旗做买卖或种地,我等遵奉定例,准其暂行寄居,奈因民人得利,便不愿回籍。窃查,民人向以内地州县为乡井,我等蒙古系世居边外藩地,治理内外向有区别。原奏为暂居蒙地之民人编立户籍,依汉法治理外藩,实系擅改钦定律例,故我等蒙众万难遵办。设如晋抚张之洞所请,编立户籍,蒙众必流离失所,迁徙他处,民人乘间开种我太祖成吉思汗陵寝、先祖扎萨克郡王、贝勒、贝子陵寝禁地,弭乱法度,遗患无穷。将此出具呈报,仰请御前行走、副盟长鉴核,并转呈应报之处,以期为圣朝建业之本部属众安生。为此呈报。光绪十年四月二十三日[17]。
这番文字表达了鄂尔多斯各旗上下对改制后果的担忧,尤其鄂尔多斯左翼三旗因直接涉及改制范围,普遍持以反对的立场,相互函商如何统一行动等事。当时副盟长、准格尔旗贝子扎那噶尔迪致函归化城副都统,表示坚决反对为寄民编户立籍[18]。但是,清政府最终还是赞同张之洞的主张,下令“绥远城将军丰绅督率土默特参领,按照当年界址,无论已开未开,绘图帖说,办理编立客民户籍,报地升科事宜”[19]。
编户立籍是使口外私垦合法化的一种举措,实际上是清末官垦的前奏。虽然这一举措在准格尔旗未能付诸实施,但很大程度上打破“春出秋归”的雁行制度的限制,从制度上为内地汉民移居塞外开辟了通道。从准格尔旗各时期农耕村落形成情况看,清代形成的113个村落中,光绪以前建村的只有27个,而光绪年间成村的却有86个[20],占清代成村比例的76.1%之多。这证明,张之洞的编户立籍虽未在准格尔旗全面实施,但有力地冲破“内省”与“外藩”的边界,为汉族移民定居准格尔打开了新局面。
四、跨塞县的形成与准格尔旗辖境的缩小
清初,晋陕两省沿边各县的辖境都在长城以内。康熙三十六年(1697),鄂尔多斯沿墙禁留地开放,允许内地汉民耕种以后,汉族移民开始进入准格尔旗境内。由于清朝对汉民进入蒙古地区持以谨慎态度,采取蒙汉分治办法,由府谷、河曲、偏关等县和托、清二厅分片管理。“放垦蒙地”以前,这些厅、县只管辖区境内的汉民,“没有归其直接管辖治理的划定行政区域”[21]。不过,“对人的统治方式也意味着对土地的统治方式”[22],清政府正是通过这样的统治方式,使原先属于蒙古王公的领地隐蔽地在向国家直接控制转变[23]。
放垦蒙地以后,清政府将准格尔旗沿墙地区直截了当地划给了临近省份。光绪三十二年(1907),垦务大臣、绥远城将军贻谷“以黑界地移民多为山西、陕西两省农民为由,决定将仁、义两段土地划归山西省管辖,礼、智、信三段土地划归陕西省管辖”[24],并将此决定通知晋陕两省巡抚,又遣准格尔旗垦务分局姚世仪,陕西省府谷县知县杨映霄到黑界地办理归属事宜。姚、杨二人到黑界地实地勘察后商定,“古城原隶陕西,仍应归陕,自古城迤西,则以古城河分疆,河南属陕,河北属晋,古城东北,则以小好赖沟分界,沟北属晋,沟南属陕”,以便征收岁租,“遇有词讼,各有专司,两省界限划清,毋许混淆”[25]。这样,“义”“礼”两段地之间的古城河、小好赖沟成了晋陕管辖区的分界线,河西礼、智、信三段归陕西省,河东仁、义两段归山西省。这就意味着准格尔旗对黑界地的实际所有权的转移,由此准格尔旗辖境大大缩小。而靠近边墙的府谷、河曲二县变成“跨塞县”。其中府谷县所占地盘最大,管辖范围南起长城,北到坝梁,西到准格尔、郡王旗的边界,内有古城、哈拉寨、沙梁三镇和塌塌坝、红荆塌等较大的村落。
官垦开始以后,州县对蒙旗的控制也加强了。在司法上,进一步扩大县的职权。清政府明确规定:“凡设治地方,所有关涉旗蒙与民人互控之案,悉归该地方官直接审理,旗员蒙员……概不得干预”[26],进而分解和消弱蒙旗的传统审案权限,特别是介入单蒙案件。“其单蒙案件,有已经蒙旗办结、冤抑未伸者,或经地方官访问,或赴地方官控告,并请准由地方官禀请提讯拟办”[27]。在司法上,由厅县起主导作用,成为实际执行机构。
注释:
[1]萨拉齐厅:雍正十二年(1731)设萨拉齐通判,乾隆二十五(1760)年改理事厅,同治四年(1865),改同知,光绪十年(1884)改抚民同知兼辖三公旗、杭锦旗、达拉特旗。托克托城厅:乾隆元年(1736)设协理通判,隶归绥道;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理事厅;光绪十年(1884)改抚民通判厅,兼辖鄂尔多斯左翼后旗地。清水河厅:乾隆元年(1736)该协理通判,隶归绥道;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理事通判;光绪十年(1884)改为抚民通判,兼辖鄂尔多斯左翼前旗地。见《归绥道志》(抄本)卷二“疆域沿革表”。
[2]《准旗档案》卷2,第75-76页,《萨拉齐通判那富蒙汉交涉之盗骗等案由萨厅受理事宜咨准格尔旗贝子文》,乾隆五十六年三月十四日。
[3]《准旗档案》卷2,第165-166页,《萨拉齐通判那富为依照所分地界分理案件咨准格尔旗贝子文》,乾隆五十六年十月。
[4]《准旗档案》卷3(上),第45页,《神木司员为蒙汉交涉案札准格尔旗贝子文》,嘉庆二年七月初五。
[5]《准旗档案》卷12,第323-324页,《托克托厅通判为分区管治汉民咨准格尔旗衙门文》,道光十六年四月十七日。注:章古图淖尔在乾隆五十六年时在今呼斯太河入黄河口边湖名,后被黄河淹没。《准格尔旗民歌选》,第206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0年。
[6]内蒙古大学历史研究所藏:《绥远通志稿》(影印本)卷63,“司法”。
[7]《准旗档案》卷28,第388-389页,《清水河厅通判衙门为会同查勘厅县与蒙旗边界咨准格尔旗贝子文》,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七日。
[8]《准旗档案》卷28,第388-389页,《清水河厅通判衙门为会同查勘厅县与蒙旗边界咨准格尔旗贝子文》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七日。
[9]《准旗档案》卷7,第200-202页,《神木司员衙门为转报厅县与准格尔旗交界情形及应在何处监禁案犯等事札咨准格尔旗衙门文》,道光七年十二月初九。
[10]《准旗档案》卷76,第55-56页,《伊克昭盟盟长为驱逐居留蒙地之民人咨清水河厅通判衙门文》,光绪二十年二月十日。
[11]内蒙古大学历史研究所藏:《绥远通志稿》(影印本)卷73,“民族·汉族”。
[12]张永江:《论清代漠南蒙古地区的二元管理体制》,第37页,载于《清史研究》1998年第二期。
[13]沈云龙主编:《张文襄公全集》卷6,“奏议六”,第674-675页,文海出版社印行。
[14]苏德毕力格:《张之洞与口外七厅改制》,QuaestionesMongolorumDisputateNo.4Tokyo2008。
[15]沈云龙主编:《张文襄公全集》卷6,“奏议六”,第683页,文海出版社印行。
[16]沈云龙主编:《张文襄公全集》卷6,“奏议六”,第684页,文海出版社印行。
[17]《准旗档案》卷65,第166-168页,《达拉特贝子索那木彭苏克、协理台吉等就民人编立户籍一事呈伊克昭盟副盟长贝子扎那噶尔迪文》,光绪十年四月二十三日。
[18]《准旗档案》卷65,第172页,《准格尔贝子扎那噶尔迪为编立户籍咨呈归化城副都统文》,光绪十年。
[19]《土默特志》上卷,第181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
[20]此外,民国时期12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0个,情况不明的有104个村。
[21]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政府志》办公室编:《内蒙古自治区志·政府志》,第98页,(北京)方志出版社,2001年。
[22]薛智平:《清代内蒙古地区设置述评》,见刘海源主编《内蒙古垦务研究》(第一辑),第7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
[23]梁卫东:《清末鄂尔多斯基层社会控制研究》,第92页,民族出版社,2009年。
[24]伊克昭盟志编纂委员会编:《伊克昭盟志》第一册,第181页,现代出版社,1994年。
[25]贻谷:《蒙垦陈诉供状》,“谨将查办复奏被参各款分晰条对呈请查核”,《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838页。
[26]薛智平:《清代内蒙古设治述评》,载刘海源主编《内蒙古垦务研究》第1辑,第74页。
[27]锡良著:《锡清弼制军奏稿》(四),第1076页,文海出版社,1974年。
(作者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年鉴刊物上一篇:【史记寻踪】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所见北疆边郡之历史面貌
- 年鉴刊物下一篇:【史记寻踪】呼伦贝尔金代长城
- 声明: 转载请注明来源于《内蒙古区情网》官方网站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